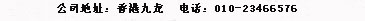胎劫惊梦兽变奠祭
胎劫
惊梦
蛇,漫山遍野的蛇,蠕动着,有的窝在洞里,死的。她都无法下脚,丈夫就走在前面,却连头也不回。她终于忍不住向前扑着尖叫了起来:
“蛇……,蛇……。”
有人搂住了她,她睁开了眼,那瘦削的脸,温情的眼,是丈夫。窗外还是黑魆魆地,地上挤进一线月影,宛如一条蛇。
“我又梦见蛇了……。”她喃喃地,靠在丈夫并不宽敞的胸前。
“蛇是儿子。”丈夫抚着她隆起地肚皮说。
“好大一片,还有好多死在洞里。”
“……”
她已记不清这是多少次梦蛇了。别人都说蛇是儿子,可她总梦死蛇。大的有缠在小山上,可那似乎只是蛇皮;小的就像丈夫的小拇指,弯曲着蜷在洞里,不知死活。丈夫说那只是梦的强制性,越怕越梦。可他却也梦。她怎么也忘不了母亲告诉她的一个关于蛇的梦。在她之后,母亲又怀了一个,不想要。便在缸沿上挤,用捶头擂,负重压,终于,那团肉被驱逐出去了。被扔在了远离家门的野滩里……。不久,母亲做了一个清晰的梦:一条似蛇似龙的东西爬进了窗子,母亲用一把铁锹砍断了它的头,它断了的头却说了人话:我要报复……!她不寒而栗,大嫂七个月小产了,七死八活,他只活了一小会儿;三哥一岁半的儿子吃呛方便面糟蹋了;难道……。她是不信冥冥中有主宰人的东西存在的。
今天是预产期,可为什么还没醒动呢?别人都说大多数产妇都会超那么几天的……。她用手摸了摸,按了按,没任何反映。肚皮上妊娠纹清晰可见,像皱纹,刻录岁月之痕。在平时,只要她一摸一按,小家伙便开始得意了,这里撑起一个疙瘩,那儿鼓起一个包。他们便常猜这是头、是手、还是臭毛脚丫。丈夫有时爬在上面和他未来的儿子说话,还亲那疙瘩。她喜欢那种感觉。
此时,他睡熟了,半睁着眼,她想推醒告诉他:胎儿不动了。可她没这样做,她也说不清为什么。窗帘动了一下。她的耳畔忽然又响起了那个瘆人的声音。她早已把母亲换成了自己,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换了。小时候的她多富有想像力啊!那时候的家,没电,她把她所看到的文字、听到的故事统统幻化成了图像封存在脑海中,让它们随时地放映。那大张地蛇的口,长长地红红地信子,夜空下对着她发出阴森地惨叫:我要报复……!她惊恐地搂住了丈夫的脖子,把脸藏在丈夫的脸上。
“乖!怎么了?”丈夫经常把她当孩子。
“咋没有胎动了?”
“傻瓜,他不睡觉了?”
“今天是预产期!”
“嗯……,明天咱去检查一下吧!”
她信服的点点头,丈夫不善言语,但他却很会决策,他不会错的。
他被打扰了两次,睡意全无,躺在床上,大脑透明的像张纸。他有些心虚。妻子梦蛇,他也梦蛇,妻子梦死蛇,他也梦死蛇。母亲的话又袭入了脑海,要他小心,尤其接近预产期了,别让她再干重活,时时步步要看好……。这都没问题,他们也早就从书上看到了,接近预产期随时都可能会有醒动。关键是母亲又说,父亲梦了一个梦:里屋的隔墙倒了。“头胎男娃娃一堵墙”,兆头不好!哎!又是梦,总是梦。他深深地呼了口气,像是要把所有的恶梦都释放了出去,再去做别的好梦。他从来不信这些,可现在……
老大夫头发花白的让人怀疑他的医术也跟头发一样苍白乏力,手抖嘴颤让人不由得怀疑他的耳聋,他听了又听,按了又按,眼睛使劲地盯着他看。他丝毫不敢动,生怕会震荡了老先生的听波,忽略了哪一个正输送出来的生命信息。
“胎心音正常!”
那终于释放出来的浊音正是圈在他自己口里已久的几个字,经老先生一放,他感觉自己倒瘪了许多。
另一处,一个年青的女医生着急地找了半天表,掐时间地给数了胎心音。热情洋溢地塞给了他们一大堆的祝福,兴高采烈地收回了他们的感激之辞。
“世上本无事,庸人自挠之。”他自嘲地笑了。
兽变
终于熬到周五了,医院,随行的大包囊括了生产的必需品:小衣服、小裤裤、小袜子、小尿布、小被被、小暖宝宝、卫生纸……,他们都是细致人,连小毛衣都有了。
两人去,三人回。他想想觉得怪怪地。
从大夫的眼中他看出了一丝冷峻,那也如老先生一般死盯着他的脸,只是那眼中多了几份捕捉的疑虑。他躲开了那冷酷的穿刺,把目光躲进了妻子的眼,那满眼的惶恐让他心疼。旁边是一个孕妇和她的家属。一个场景突然清晰地在他脑海放映:一个陌生的家庭,一家人站的、坐的,医院里的事,……一对年轻夫妇,孩子在预产期的晚上死在肚子里了,俩人哭得……。他惊诧地扭头看着旁边的孕妇,她的手习惯性地卡在后腰两侧,整个人就像一个胀袋的香肠。该死!发布新闻的就是她!给家人讲得急切、仔细。他瞪了一眼,狠狠地转过了头。大夫还在使劲地按着那死鼓鼓的肚皮,他似乎感觉到里面的僵硬。他有点想吐,早晨没吃饭便赶来了,准备检查完之后到外面去好好吃一顿积攒力量。
一切都在他的预感与预想中,事情也顺着他的想像而来。他像是导演一样,又心领神会的扮演着他的演员角色,按部就班地揽过妻子,理所当然地哭泣着,顺理成章地擦拭着妻子的泪,陈式地无所适从着、呆立着。这个镜头完了,他自然地进入了下一个镜头,柔柔地扶妻子坐下,果敢问医生怎么办。大夫交给了他两小片白白地药,嘱咐着:每次四分之一片,两小时一吃,两小时一吃……,把它打下来!他像影片中的勇士,刚毅地点点头,回转身再无所适从地扶着妻子的肩。妻子静静地靠在他的胳膊上,两手软软地搂住他的腰,轻轻吸着鼻子,慢慢立起身,低声说:
“走……!”
药片真小,他擅抖而有力地把它分成了四牙,四分之一的药片只有米粒大小!
“咱们……吃吧!?”
妻子紧紧地把头埋在了他的怀里,抽噎着:
“我不吃……!”
他哭出声了。这是在残杀亲骨肉吗?他想着这药的威力,会像大棍一样,没头没脑地砸下,砸下,砸下……,砸出那本可以称做自己儿子的那团肉。他会血肉模糊吗?他会被伤成什么程度?不吃下,那似乎有还不曾了断的亲情,那还是他们的宝宝,小家伙;吃下,则一切都就此结束了,那是他们的敌人,一个瘤子,一团没生命意义的赘肉!
一切的完结也就从这“米粒”开始了!不再有小生命,不再有温顺地妻子。她们被抛入了魔兽的世界,去面对面的拼杀、厮咬,像两只狼,两只争夺一条生命的狼。没有人能帮得上她们,也没有人阻止她们。一只隐在暗处,一只现于明处。
她狰狞着,嚎叫着,来回踱着凶险的步子,蹲下,站起,站起,蹲下。龇着白森森地牙,瞪着血红红地眼,披着散乱乱地发,有几回他都几乎成了她的攻击目标。他的胳膊终于被咬了一下。他想到了妻子经常说的“复仇”的梦,他觉得她是那只困兽的幻影,或者根本就是那复仇的“蛇”!他退缩着,不敢朝前,不敢碰她,不敢正视那偶或瞪向他的阴毒的蛇眼,任由她满地的逡巡,蛮横地撞击。已是夜间十二点多了,他想到了哈姆莱特的一句台词“已是黑夜了,狼在嚎叫,鬼在哭泣。”他的头皮麻麻地。
……
“刚才咬疼了吗?”一个声音颤颤地、悠悠地,像落在了头顶上的雨。
她居然恢复了人性!
他看那眼,弱弱地,柔柔地,心头掠过一丝欠意,忙忙地揽住她说:“没咬着。这会儿怎么样啊?”
她长吁了一口气,算做回答。
突然,他听到了“嗞……嗞……”猛猛地吸气声,像蛇一样,一双手死死地扣在他的肩上,掐得他生疼,他赶紧往下耸。她却蹲下去,蹲下去……。他把手拭探性地放在她湿漉漉地头发上,她猛一甩头,回过了脸,他向后趔趄了一步:五官什么也看不见,乱发罩在脸上,两束凶光穿发而出,追向那退闪不及的手。
“下来了,快叫医生……!”
他逃也似的窜出了门,求救般地奔向医务室。
奠祭
一个拳头大小的黑糊糊的东西被夹在了两腿间。慢慢地,还在逐渐变大,后面还会有什么?未知的怪物啊!它并不宣布它的失败,它已经在那停留了好十几分钟了。随着她的一声凄厉地怒嚎,它终于滑出来了,像蛇一般,一团带黑顶的粉肉!它感觉到它的失败了,它也意识到了它将有的下场,它变了,恢复了它的可爱——一个完完整整地、黑头发、红嘴唇、有着小毛手和小毛脚丫的小东西。它不是狼,不是蛇,是人形!是可爱地本可以做他们最疼爱的儿子的人形。它没被打得血肉模糊,或者根本就没受到任何伤害。它是在博取人类对它的同情和怜爱?那小红嘴仅有指头蛋那么大,那小脚连两根手指的宽度和长度都没有,小脸润透,小手绵软,可爱的小身躯,可惜欠缺了人最美的东西——灵魂。它只是伪装了的魔鬼!他想到了电影中的吸血僵尸,那么红的嘴唇。他又一阵的恶心,想吐,却没吐出来。
妻子已是沉沉地睡去了,眼角挂着泪便沉睡了,没看一眼跟她做了十个月怪的那可爱的小东西便睡了。可怜,无奈,她累了。他没给它穿衣服,连一片尿布也没给它裹,只是用纸包了一下便扔在了床下。外面太黑了!
露天的公厕是蛆虫的乐园。那黄浊的潭浆上厚厚地铺了一层蠕动的蛆虫,就像梦中的蛇群。他抓住那小腿,把它倒栽进了那乱攘攘地“白蛇群”中,转身就走。头有点晕,刚才牙直打颤,咬得头痛。他这才感觉到早晨的凉意了。回到屋子,弱小的妻子脸色惨白地睡着,是那小红嘴吸走了她的血吗?床下空荡荡地,他呢……,那个可爱的他呢?他又想到了那小红嘴,红得那么可爱!当时,他还有过想要亲一亲的欲望……。他又一阵的恶心,猛地冲出了屋子向公厕跑去,顺路买了一瓶酒。
朝晖斜映,朝天,那只脚,粉粉地,倒立着。潭面,一个孤独的小影依偎在娇小的它的跟前,一样柔,一样的美!一样的凄婉!他拉出了它,顺腿撕掉了纸,用酒猛喷猛洗,酒和泪混在了一起,浇下了它身上的污浊,也冲走了爬上它身的蛆虫!他包起它,捧着,走向荒野,找到了一棵三面有小树,周边草茂密,中间凸起的小土梁,放下了它,把剩余的酒,全洒在了它的身上。二十四个小时前,他还是他们的希望,像储君一样的高贵,他是他们的准儿子;十二个小时前,它是他们的敌人,向他们索命的吸血鬼;而现在,它是他们的什么……
腋下,一个蛆虫被淋了出来,蠕动着那丑陋的躯体爬上了它的胸。他瞪着那肮脏的生命,不知道是该弄死它,还是该留下它。那生命慌乱地扭动着,展示着它的存在。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,也不知道是谁把它劫掠到这儿,却还给它保留了一份生的希望。
#小说#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eqimingxing.net/tpszzl/979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