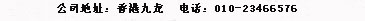苦虫第二章双生
《碗子肉》
碗子肉,就是香。猪肉荤,放生姜;红薯甜,浇蜂糖。一嘴油,一嘴糖,吃饱上山能打狼;先牙疼,再滑肠,疼毕拉完心还想,一顿不吃闹得慌……
双生本来有个孪生哥哥,叫孪生,兄弟俩生下来没几天,因为抢奶吃,双生就把哥哥孪生踹下火炕,摔死了。
村里的长辈都说,双生是为了吃“独食”,才踹死了哥哥孪生。不过,双生的“独食”也并没有吃多久——为了给家里储备劳力,双生的母亲,又怀上了。
在往后的10年里,双生的母亲,差不多以一年一胎的速度,连续给双生添了九个兄弟姐妹。
双生最小的妹妹“垫窝子”出生那年,碰巧赶上三年自然灾害,村里人,陈粮吃完了吃新粮、新粮吃完了吃野菜、野菜吃完了吃树叶、树叶吃完了吃树皮……最后,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,连救命的种子也吃了。
“垫窝子”一生下来,母亲就饿得没了奶水。村里一些二流子就胡乱造谣,说双生母亲的奶水,都是被双生父亲偷偷吃掉的。其实,这种谣言,除了其他二流子,大家肯定都不信,因为大家都知道,双生的父母,都是正派人,不会干这种龌龊事。
因为没有奶水,双生的父母,只能熬些“榆树面”糊糊给“垫窝子”吃。结果,没吃几顿,“垫窝子”就被活活撑死了。
“榆树面”这种东西,又糙又硬,既难消化,又容易刮伤肠胃,而且一到肚子里,很快就会变成疙瘩,蹲茅坑的时候,不见血不出来。
吃这种东西,别说刚出生的小孩,就算是龙精虎猛的年轻人,也被撑死了不少。有些人吃了“榆树面”,蹲在茅坑拉屎,结果连屎带肠子,一起拉了出来,再往回塞,还没塞到一半,人就疼得断了气。
关中地区,养狗的人家,把同一窝狗崽里最小的一只叫“垫窝子”,双生最小的妹妹,死得太急,来不及起名字,就得了这个不中听的绰号。
双生的父亲,领着双生,像扔死猫死狗一样,拎着一条腿,把“垫窝子”扔进了臭气熏天的旱厕里。末了,双生的父亲长叹一声,自言自语似地说道:“娃呀,爸也没想到,把你生下来,竟然是给庄稼做了贡献。”
虽然跟“垫窝子”做兄妹的时间很短,但是“垫窝子”的死,以及“垫窝子”被扔进旱厕的景象,却深深地刺激到了双生。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只要一蹲茅坑,双生就总会感觉到,好像有一只手在摸他的屁股。
处理完了“垫窝子”的事情,一家人全部聚集在了火炕跟前。
双生的母亲,面如死灰,盘膝坐在被灶火熏得乌漆麻黑的火炕上:眼窝深陷,双目无光如死鱼;颧骨暴突,脸上无肉赛活猴;头发灰白稀疏,挽起单抓髻细如枯柳枝;牙齿脱釉开裂,张开菱角嘴碎似干秕谷;肩如横衣竿,趴着猴似的八哥;臂似弯拐棍,抱着猫样的九妹。
大灾之年,能够饿着肚子活下来的,十有八九,都得“脱相”。
见人都到齐了,双生的母亲,一句三喘地对孩子们说道:“咱家现在没吃的了,连榆树面,也没有了。贺家坡的贺把抓,早上来咱家了,说他家有吃不完的大白蒸馍,让我问一下你们几个,谁愿意去。”
“我!”、“我去!”、“我愿意!”……听到有吃不完的大白蒸馍,孩子们都争先恐后抢着要去。
八哥口齿不清地呢喃道:“妈,我也想去。”
刚学会说话的九妹仰起脸,一个劲儿地喊:“妈,妈,妈,馍!馍!馍!”
看着怀里的九妹,双生母亲苦笑了一下,柔声说道:“九妹,你最小,妈本来想让你去,但是你把抓叔只要男娃,不要女娃。”
双生忽然问道:“妈,吃了大白蒸馍,还能回来不?”
只见双生母亲,忽然将脸埋到前胸,哭了起来:“不要回来,千万不要回来,回来小心挨打!”
听母亲这么一说,所有孩子都低下了头,不再吭声。
双生:“去的有大白蒸馍吃,没去的有不?”
双生的母亲抬起头:“有!不管谁去,咱家都有大白馒头吃!谁愿意去?”
话刚讲完,除了双生,其他孩子都赶紧往后退了几步。
双生母亲:“双生,你最大,你去行不?”
双生忽然“哇”的一声,哭了出来,大喊道:“老八小,不认识路,送过去跑不回来,你让老八去!”
双生母亲:“老八太小,在我身边时间也短,妈舍不得,你就……”
双生:“我不管!我不去!老八小,老二、老四、老六都不小,他几个都可以去,反正我不去!”
双生母亲:“贺家坡不光有大白蒸馍,还有碗子肉,油汪汪的猪肉,盖着黄灿灿的拔丝红薯,上面的蜂糖,有两寸多厚……”
双生:“有碗子肉我也不去!我就想待在咱家,我不想当野种!”
“行!娃他爸……”双生母亲,向双生父亲招了招手,然后别过脸去。
双生父亲心领神会,从后面,一把将双生摁倒在地,然后一只手从自己鞋上抽出鞋带,将双生捆了个结结实实。
双生父亲:“让你去,你就去!敢说个不字,就把你跟垫窝子一样,扔到茅坑里……”
第二天,天还没亮,贺把抓就挑着两个盖着甑布的大箩筐,在水担的“吱扭”声中,探头探脑地踅摸进了双生家里。
见贺把抓进了屋,双生母亲,坐在炕上,屁股连抬都没抬,朝后院喊了一声:“娃他爸,你把抓兄弟来了!”
双生父亲应声进屋,对贺把抓点头哈腰连连问好。
贺把抓拍了拍双生父亲的肩头,说道:“哥,看兄弟都给你带了啥好东西。”说罢,一把撤掉了盖在箩筐上面的甑布。
甑布撤掉,一筐是热气腾腾的大白蒸馍,另一筐是甜香四溢的拔丝红薯,将双生家的四个馍笼,盛得满满当当。
看到大白蒸馍和拔丝红薯,孩子们挤在一起,脖子伸得跟罗斯鸡似的,一个劲儿地狂咽口水,但是谁也没敢向前挪动一步。
看到孩子们一动不动,贺把抓呲呲嘴,皮笑肉不笑地朝孩子们打招呼:“来来来,都来吃。”
孩子们还是不动。贺把抓朝双生父亲咧嘴一笑,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:“哥,你家的家法严得很么,嘿嘿!”
双生父亲尴尬一笑,低声回答道:“都是娃他妈管教的,我说了不算……”
贺把抓转头换上满脸的堆笑,开玩笑似的朝双生母亲大声说道:“掌柜的,给娃们发个话么!”
双生母亲终于抬了一下屁股,朝几个孩子轻声说道:“吃!都吃去!蒸馍和红薯,爱吃啥吃啥。”
得到母亲的“命令”,孩子们一拥而上,好一顿狼吞虎咽。
双生父亲捡起一只蒸馍和一只红薯,咽了咽口水,走到双生母亲的跟前,还没等递上去,双生母亲就猛地把头别了过去。
就在这时,躺在双生母亲怀里的九妹,忽然哭闹起来:“妈,妈,妈,馍!馍!馍!”
双生父亲好言劝慰道:“娃他妈,吃一口吧,你不吃,九妹也得吃。”然后放下馒头和红薯,又朝后院去了。
不到一分钟功夫,双生父亲又进了屋,双手提着被五花大绑、大哭大喊的双生。
双生父亲:“还嘲嘲?想进茅坑的是?!”
一提到进茅坑,双生果然住了声。
经过母亲身边时,双生忽然又哭喊起来。
双生:“妈,我又不是野种,为啥偏偏拿我换蒸馍红薯?为啥?为啥呀?!”
看到双生浑身的泥垢和布满血丝的眼珠子,双生母亲,心里不禁难受起来,赶紧说道:“娃他爸,让我跟娃说两句话!”
双生父亲“嗯”了一声,将双生轻轻放在双生母亲跟前。
双生母亲:“双生,现在咱家困难,一家子能不能活下去,都是问题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你不要怪妈,过去了要好好听话,不要往回跑,妈有空了就过去看你,你要相信妈,熬过旱灾,就会苦尽甜来……”
双生母亲自己说自己的,双生也不搭话,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哭大喊。
旁边的贺把抓听得有点不耐烦了,朝双生父亲挤了一个眼,双生父亲面如死灰地点点头。
只见贺把抓一把拎起双生,像挑猪崽一样挑在水担的一头,另一头挑了两只空箩筐,招呼了一声“哥、嫂子,兄弟走了”,便伴着水担的“吱扭”声、双生的哭喊声,唱唱哼哼走出了门口。
等水担的“吱扭”声、贺把抓的唱哼声、双生的哭喊声都听不见了,整个屋子,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,只剩下孩子们大口咀嚼馒头红薯的“吧唧”声。
“吃!吃!吃!苟日的光知道吃!这些蒸馍红薯,都是用你哥换来的!你哥走了,苟日的,都不知道打声招呼、送一下!”双生母亲,越说越气,最后竟然体力不支,头往后一仰,晕了过去。
双生父亲赶紧上前抱住双生母亲,然后让几个孩子把红薯在水里捏成了糊糊,掰开双生母亲的嘴,将红薯糊糊慢慢灌了下去。
双生被送走不久,关中地区果然“苦尽甜来”——倾盆似的大雨,连续下了三天三夜!一直下到井里满了,塘里满了,河里也满了。
雨刚一停,村里人就急不可待地下犁种地,有种小麦的、有种大豆的、有种玉米的、有种洋芋的、有种红薯的、有种南瓜的……总而言之,有啥种啥,也不管应不应季。
看到村里人都在地里热火朝天的忙活,双生父亲,又开始后悔自己当初把双生送出去的决定。
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,双生父亲总是向双生母亲,不停地嘟囔:“要是再忍两三个月,双生也不用去贺家坡受苦了,都怪我太糊涂……”
不过,只嘟囔了两三年,就不嘟囔了——人没了。双生父亲,在奶牛场挤牛奶的时候,被奶牛踢中了心窝,把心给踢散了,医院,就断了气。
后来,九妹为了给父亲“报仇”,一个人偷偷溜进了奶牛场,往“杀人奶牛”的食槽里扔了一把缝衣针。
奶牛吃东西,本来就口粗,啥东西都往肚子里咽。这些缝衣针,基本上都没浪费,有的扎在嘴里、有的扎在喉咙里、有的扎在气管里、有的扎在胃里……头天晚上放的缝衣针,第二天中午,奶牛场就支起大锅,在炖牛肉了。
跟普通的牛肉不同,奶牛的肉,自带一种奶香,有些人吃了,特别容易“上瘾”。由于这个原因,后来奶牛场的牛,每隔一个月,就会死掉一头,全部都是吃了缝衣针死掉的,然后奶牛场就又开始支大锅、炖牛肉。
不到两年,奶牛场就倒闭了——奶牛全死光了。
父亲去世前,双生回过三次家,都是在被送走后不久。
每次回家,双生都是浑身的伤。前两次,双生都是带着伤被父亲毒打一顿,然后用井绳捆着送回贺家坡的。最后一次,父亲正要打,双生母亲忽然说话了:“别打了,让我给娃说两句话。”
双生母亲摸着双生的头,柔声问道:“你咋又回来了?”
双生抽抽嗒嗒地回答道:“我想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六、老七、老八、老九!我想我爸!我想你了!”
一句话说得双生母亲心里不禁一酸,伸手就把双生抱到了怀里:“娃呀,为了咱这个家,你受罪了,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了,你再回来,贺把抓驴打滚地讨债,咱家吃啥?老八、老九吃啥?”
听母亲这么一说,双生止住了哭声,从裤裆里摸出一吊猪肉,递给了母亲,然后说了一句“妈,我走了!”扭头就走。
双生母亲,在后面追着喊:“记住,再苦的日子,都会苦尽甜来的。”
双生的弟弟妹妹们,也你一句“哥”、我一句“哥”,紧紧跟在后面。
双生走出门口,他的弟弟妹妹们还想跟着,却被双生父亲一把拦住。双生回头看看身后,神情失落地回了贺家坡。
双生走后,双生母亲开始责备双生父亲:“娃他爸,你跟贺把抓到底算啥亲戚?你看把娃打成啥样子了?而且娃在贺家坡挨完打,回来还要挨你的打。”
双生父亲叹了口气,缓缓回答道:“其实把抓也是一个可怜娃。把抓刚十四的时候,他隔壁黑女子早熟,非要拉着把抓睡觉,结果被黑女子他爸发现了。黑女子反咬一口,说把抓耍流氓,黑女子他爸脑子一热,一把把把抓的俩蛋核给捏爆了,把抓他家就因为这个断了香火。把抓为啥叫把抓?都是村里的二流子乱叫,叫出来的,真名其实叫炳彰。后来,把抓的性格就变了,逮住蛤蟆拧腿、逮住鸡娃扯嘴,不管啥毛虫虫,到了把抓手里,都得遭殃。为了不让先人留下来的家财,在自己手里踢散,把抓抱养过好几个碎娃,结果都被打得受不了,跑了……”
“那你还让双生去?!”双生母亲,愤怒地问道。
双生父亲,赶紧好言解释道:“我也是看大家都是亲戚,不会下死手,而且把抓也说了,娃不跑,他肯定不打,娃要是跑,不打肯定也不行……”
双生父亲下葬那天,贺把抓带着双生来了。贺把抓牵着一头驴,驴肚子两侧各挎一个箩筐。一边箩筐里装着白花花的碱水豆腐,一边箩筐里装着绿莹莹的碧玉白菜。双生左手拽着驴尾巴,右手提着臭粪篓,眼巴巴看着驴屁股,生怕漏接了哪怕一粒驴粪。
到了双生父亲灵前,贺把抓突然甩掉驴绳,猛地一扑,直挺挺地趴在地上,震天响地喊了一声“哥呀!”,干嚎没眼泪。
嚎了半天,发现双生不在身边,贺把抓转脸冲着驴屁股骂了一句:“苟日的,还不过来!这几年的粮食白吃了?!”
双生眼里噙着泪水,紧咬牙关,一步一步挪到了贺把抓跟前。
贺把抓忽然“噌”的一声,从地上蹦了起来,伸手朝双生的后脑勺,“啪”的一声,重重抽了一巴掌,直接就把双生抽倒在了地上。双生“哇”的一声,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。
双生母亲赶紧上前抱住双生,哑着嗓子安慰道:“我娃可怜,我娃别哭了……”
双生抽抽嗒嗒地问母亲:“妈,到底啥时候才能苦尽甜来?”
双生母亲,轻轻拍了拍双生的后背“等你长大了,自然就苦尽甜来了,我娃你放心……”说完站起身来,朝贺把抓脸上“乒啪”就是两巴掌。
贺把抓挨了揍,正要还手,双生的堂叔堂伯一拥而上,纷纷睁眉豁眼地问道:“想干啥?在我村还想撒野?”直吓得贺把抓赶紧缩了回去。
双生母亲晃着食指,大骂贺把抓:“你个有球没蛋的杂种,在你贺家坡打我娃,到了我村,在我娃他爸灵跟前还打我娃,谁给你苟日的胆子?苟日的哪来的回哪去,把我娃留下!”
贺把抓打人的胆子虽然没了,但是砸自己东西的胆子,还是有的。
只见贺把抓一把掀翻驴背上的两个箩筐,拌着地上厚实的黄土,把白花花的碱水豆腐踩成了稀泥,把绿莹莹的碧玉白菜跺成了浆水。边踩边跺边骂:“过锤子过事!死乞白赖过来送个不要钱的菜,好心当成了驴肝肺,欠了我的一千斤白面、一千斤红薯,现在就还我!”
贺把抓一翻旧账,所有人都傻眼了,只能眼睁睁看着双生被揪着耳朵拖走。
旱灾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年,但是双生的九个弟弟妹妹也长大了。孩子一大,吃的就多,很快就把家底给吃空了。没有办法,双生的母亲,只能让大的照顾小的,自己则背着一个破背篓,翻岭上塬,去人少地多的地方乞讨要饭,养活一家。
有一天,双生母亲外出乞讨,因为漫天大雾,走迷了路,迷迷瞪瞪,就上了贺家坡。
在一个独庄子,双生母亲看到一个赤膊的少年,双手拎着泔水桶,健步如飞地穿梭在灶房和猪圈之间。
双生母亲赶紧上前,哈着腰小声央求道:“好心的小伙子,有吃不完的剩饭剩馍,给咱打发点。”
听到声音,小伙子一回头,不由得浑身一个激灵,“咣铛”两声,扔掉了手里的泔水桶,赶紧将双生母亲搀扶起来。
只见小伙子泪流满面地叫了一声“妈!”,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双生母亲,一脸疑惑地盯着小伙子,也是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小伙子止住悲伤,一脸疑惑地说道:“妈,我是双生!你这是咋了?”
双生母亲:“你是双生?我的娃呀,妈咋要饭要到你家门口了?”说完哆哆嗦嗦哭了起来。
就在这时,灶房旁边的柴房里,传出了两声咳嗽,紧接着又是一阵拖泥带水的吐痰声,然后有一个沙哑的声音问道:“双生,谁在外面?你跟谁说话呢?”
双生赶紧扭头朝柴房大声回答道:“一个要饭的老婆子,我现在就把她打发了!”
柴房里:“啥都不要给,要饭的一个个都是懒怂,谁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!”
双生:“对,知道了!”
双生母亲指着柴房问道:“贺把抓?”
双生点了点头,将母亲拉到了猪圈旁边。
到了猪圈旁边,在十几只大肥猪“吧唧-吧唧”的吃食声的掩护下,双生再次问道:“妈,这到底是咋了?你咋要饭呢?”
双生母亲长叹了口气:“唉,有啥办法?你几个兄弟、妹子,现在饭量比我还大,家里不够吃了,你爸又不在了,妈不要饭,还能咋?”
双生轻声安慰道:“妈,你放心!只要有你娃在,咱家就有吃的。你等一下,我去给你拿吃的。”
双生说着就要往灶房走,结果被母亲一把拉住:“双生,你等一下,你跟妈老实说,贺把抓还打不打你?”
双生爽朗一笑,回答道:“以前经常打,现在不打了,打不动了,连下炕都难!”
双生母亲:“咋连坑都下不了了?”
双生:“瘫了!就头稍微能动。以前经常打我,我嘴上不说,但是心里一直咒他死快点,结果还真灵,现在半死不活的,我看也差不多了……”
双生母亲听完,一脸惊诧地说道:“娃呀,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,不管咋说,你都是吃人家的、住人家的,人家好歹也算是你的一个大人,你咋能有这样的心思?”
双生拍拍母亲的双手,柔声说道:“不管这些了,我给你拿蒸馍红薯去。”说完,径直去了灶房。
等双生端着蒸馍红薯再出来时,母亲早就没了踪影。
一个母亲,要饭要到被自己弃养的孩子家门口,这样的刺激,双生母亲根本就无法承受。
双生母亲背着空背篓回到家里,全家十口,三天就分吃了一个巴掌大的黑面蒸馍,以及一大锅没有任何调料的刺荆面粉拌汤。
回到村里,双生母亲就四处寻找贺家坡替人牵牛耕地的徒雇,打听双生对待贺把抓到底咋样。
结果,这些老实巴交的徒雇,纷纷对双生竖起大拇指,说自从贺把抓瘫在炕上,双生天天端饭送水、擦屎接尿,虽然不是亲生的,但是简直比亲生的还要孝顺。
听徒雇们这么一说,双生母亲才完全放下心来。
第四天早上,天还没亮,双生母亲就听到有人敲门。打开门一看,只见双生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短褂、肩上扛着生铁铧犁、右手牵着短角黄牛、左手拎着提花布包,一脸的笑意。
双生母亲:“呀!你咋来了?赶紧进屋,赶紧进屋!”
看到这张已经相当陌生的脸,双生的弟弟妹妹们,睁大了眼睛,不敢说话。
双生母亲赶紧介绍:“娃们呀,咋都不认识了?这是你哥,双生!”
“哥!”、“哥!”、“哥!”……除了最小的九妹,其他孩子,全跑了过去,将双生团团围住。
双生将黄牛拴在门口的石墩上,卸下耕犁,拎着布包,在弟弟妹妹的簇拥下进了屋子。
屁股还没沾到板凳,双生就先打开了布包,从里面摸出一包红薯干,一人一块,分给了几个弟弟妹妹。见九妹一个人蹲在墙角啃手指头,双生就捏了一块红薯干走了过去。
“九妹,咋?不认识我了?我是你哥。”一边说着,一边将红薯干喂给九妹。
双生母亲:“双生,你这是要去哪里做徒雇?”
“就在咱村!”双生一边答话,一边从布包里摸出一包粗盐、一罐蜂糖、一吊猪肉,一一递给了母亲。
双生母亲:“盐和蜂糖,都可以,猪肉太贵了,下次就不要带了!”
双生:“妈,你不用管,你娃现在苦尽甜来了,这些东西,小意思……”
听到“苦尽甜来”这四个字,双生母亲,心里不禁“咯噔”了一下:“贺把抓不在了?!”
双生尴尬一笑:“那倒没有,我一个月给隔壁一斗麦,让照顾贺把抓一顿中午饭,晚上回去,我再给做一顿。”
双生母亲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:“这样其实也可以。”
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聊了一会儿天,双生母亲忽然提议:“如果今天没活,我给咱做碗子肉,你几个兄弟妹子,长这么大,还没吃过碗子肉呢!就是家里没米没面,吃了容易滑肠……”
正说着,村长提着一个馍笼过来了,还没进门,就大声吵吵:“双生,叔给你送徒雇钱来了!”
看到双生母亲,村长笑容满面地说道:“这次双生一来,你家算是苦尽甜来了。”说完,村长便揭掉了盖在馍笼上面的甑布。
甑布底下分了两层,上面一层是大白蒸馍和拔丝红薯,下面一层一边是粳米一边是白面。
不到一个小时,全家十一口,就围在桌子上吃起了碗子肉。双生吃的很少,肉全部夹给了母亲和弟弟妹妹,自己只吃了几块红薯干。
吃完饭,一家人聊起了这些年各自的过往。双生告诉母亲:“贺把抓爱吃猪肉,尤其是碗子肉,顿顿都吃,而且专门先挑肥的吃,家里一年养十几头猪,至少有两头要被贺把抓吃掉。最后,猪肉吃太多,吃成脑梗,瘫了!”
一直都不吭声的九妹,忽然来了一句:“哥,那你咋没吃成脑梗?”
屋子里顿时笑倒一片。双生笑着回答:“哥不爱吃猪肉,哥爱吃红薯跟大白蒸馍!”
九妹:“那我吃了猪肉会不会变脑梗?”
双生:“不要吃太多就行。”
九妹:“那我就少吃一点,给咱妈多吃一点,把咱妈吃成脑梗,咱妈就不用到处跑了,就能好好在家抱我睡觉了。”
屋子里又是一阵大笑。
太阳正西的时候,双生起身要走,双生母亲让带些蒸馍和剩下的米饭回去,省的重新又要做,双生笑着回绝了。
在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,双生都在“娘家”村里做徒雇,晌午最热的时候,就在“娘家”吃顿饭,太阳正西就回贺家坡。回到贺家坡,给贺把抓做晚饭、喂贺把抓吃饭、给贺把抓擦洗身子、刷锅洗碗、拌料喂猪,一直忙到煤油灯快要烧干,才能干完。
双生去一次“娘家”,“娘家”就多一馍笼粮食。有时候是大白蒸馍、有时候是葱油锅盔、有时候是红薯面粉、有时候是油盐酱醋,如果碰到村长进屋,肯定会有一小袋东北粳米。
一个月下来,双生“娘家”的半个屋子,堆的都是吃食。双生贺家坡跑“娘家”、“娘家”跑贺家坡,一个月下来,也瘦得都快飞起来了。
有天晚上,双生正在给贺把抓擦洗身子,擦着擦着,贺把抓忽然哭了:“双生,你真是个好娃!”
双生手下停都没停,只是轻声“嗯”了一下。
贺把抓:“我就不应该打你,不应该把你当丫鬟使唤,不应该我吃肉只让你吃红薯,我现在瘫了,这都是报应。”
双生又“嗯”了一声。
贺把抓:“我给你说了个对象,曹洼的猛女子,你见过,她爸她妈今年刚没了,家里就剩下她一个。性子有点野,但是家里、地里的活,干得利索,过两天你见见?”
双生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:“我现在没时间,过阵子再说。”
贺把抓长叹了一口气:“唉,都是我不对,你心里有气,我知道……”
第二天晌午,双生正在“娘家”吃饭,一个身体壮实、小麦色皮肤、脸蛋颇为清秀的女孩子,径直走进了屋子。
女孩子:“双生在屋么?”
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,双生赶紧回头,但是一看到来人,双生又忍着没有说话。双生母亲赶紧站起来,客客气气地问道:“女子你是哪里的?找双生啥事?”
女孩子大大方方地回答道:“我是萌子,曹洼的,你叫我猛女子就行,我是双生的对象,我把抓叔叫我过来跟双生见个面!”
屋子里顿时轰笑起来,双生的弟弟妹妹们,七嘴八舌地瞎起哄:“嫂子来了!”、“咱哥有媳妇了!”、“咱有嫂子了!”、“咱哥的媳妇主动送上门了!”……
看着猛女子,双生母亲是满心的喜欢,赶紧让猛女子坐下来一起吃饭。
双生却吃不下了,因为他知道,贺把抓给他找对象,就是为了把他拴在贺家坡。
太阳正西,双生照例跟“娘家”人告别,独自回贺家坡。猛女子拽着双生的袖子要跟着,结果被双生一把甩开。
双生:“女娃要有女娃的样子!我跟你又不熟!”
猛女子:“我不管!我就要跟着你,把抓叔说了,我现在就是你的人了!”
全家又是一阵轰笑。
双生母亲:“双生,你就让猛女子跟你一块回去,听妈的话。”
双生的弟弟妹妹:“一块回去!”、“把我嫂子带上!”、“路上有狼,给我嫂子打狼!”……
双生扭头看看猛女子:“你家在曹洼?”
猛女子点点头:“嗯!”
双生:“行!到了曹洼你就回去,不要继续跟着。”
猛女子点点头:“行!”
说罢,双生就被猛女子拽着袖子,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屋子。
双生母亲看着两人的背影,脸上不由得乐开了花:“我娃这次总算是苦尽甜来了。”
到了曹洼村口,双生摆摆手:“行,到了,你自己回去吧!”
说完,转身正要走,猛女子忽然扑了上去,从后面抱住了双生,一顿乱摔。
猛女子:“把抓叔说了,我现在就是你的人了,你也就是我的人了,我还能让你给跑了!”
双生接连被摔了三个跟头,气急败坏地大骂道:“摘尼玛!放手,赶紧放手!”
猛女子哪管这个?直接把双生像抱粮食口袋一样,抱了起来,扔到路边草深的地方,然后压在双生的身上,把双生给“糟蹋”了。
最后,双生乖乖地带着猛女子回了贺家坡。
第二天,猛女子跟着双生,一起到了双生的“娘家”村。双生做徒雇,猛女子在双生“娘家”帮忙择菜做饭、洗洗刷刷。
没过多久,猛女子的肚子就大了起来。双生母亲赶紧跑了一趟贺家坡,跟贺把抓商量,让双生和猛女子赶紧把婚给结了。
双生母亲:“双生在我村做徒雇,在我家堆了半屋子米面粮油,正好在我村摆酒!”
贺把抓:“摆酒没肉不行,我家猪圈还有十几头猪,过两天杀两头,直接就在我家办了。”
双生母亲还想力争,只见贺把抓冷冷地说道:“双生在我家这么多年,吃喝拉撒,也应该姓贺了,我一直没让改姓,就是看在双生他爸——我哥的面子上!”
双生母亲顿时失去了再去争执的底气。
双生最终也在母亲的苦劝下,在贺家坡,跟猛女子摆酒完婚。
不过,就在婚礼结束的当天晚上,出了一件特别闹心的大事——贺把抓死了,被一泡猪尿给活活憋死了。
当天晚上,送走了所有宾客和同村闹洞房的二流子,一家人正准备叉门睡觉,猪圈里最肥最壮的一头大肥猪,悄悄地溜进了屋子,跳上贺把抓睡觉的火炕。
贺把抓已经蒙着被子睡着了,听到“哼唧-哼唧”的猪叫声,缓缓从被子底下挤出脑袋,结果正好跟大肥猪四目相对,贺把抓吓得大喊大叫:“猪!猪!猪!猪跑了!”
双生和猛女子,听到喊声,赶紧跑了过来,把大肥猪赶下了炕。两人要看贺把抓有没有受伤,贺把抓说没事,让两人赶紧去追猪,两人就赶紧去了。
双生和猛女子出去追猪,屋子里就剩下贺把抓一个人。贺把抓把脑袋缩回被子,继续睡觉。睡着睡着,忽然感觉到脸上湿答答、热乎乎有一股臊臭——原来,跳上炕的大肥猪,在贺把抓盖的被子上面,尿了一泡!
贺把抓本来就瘫得只有脑袋稍微能动,脸上蒙了被猪尿浸透、变得沉甸甸的棉花被子,再想动,根本就不可能了。
双生和猛女子,花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,才追到了猪。把猪赶回了猪圈,给贺把抓回了话,见贺把抓没有回应,两人就去睡了。
第二天,猛女子要给贺把抓擦脸,叫了好几声,都没有回应。猛女子小心翼翼地揭开被子一看,顿时就傻了——贺把抓像个吊死鬼一样,眼睛爆突,脸色铁青,就是舌头没有伸出来而已。
贺把抓一辈子爱吃猪肉,最终还是栽在了一泡猪尿上面。
双生办完喜事办丧事,从头至尾,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情绪变化。
给贺把抓哭灵,门人们不管有没有眼泪,至少一个个都嚎得哭天抢地,唯独双生一个人毫无反应。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,也就没说什么,只有猛女子有点气不过,说双生这个人心太毒,死了肯定也没有人哭。
大概过了半年,有一天,猛女子口渴,从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,“咕嘟-咕嘟”就往肚子里灌。刚灌了不到半瓢,猛女子的小肚子,就像刀扎一样绞痛,用手一按,“噗通”掉出来一个,再一按,“噗通”又是一个,一男一女,一对儿龙凤胎。
绝大多数女人,生了七胎八胎,再生的时候,还跟闯鬼门关似的。猛女子倒好,第一次生,就跟窜稀拉屎一样。
不过,两个小孩,身型真的是蔫巴瘦小,幸亏身上没长黄毛,要是长了黄毛,活脱脱就是两只黄鼠狼托生。
孩子一生下来,双生想都没想,给男孩取名叫“苦尽”,给女孩取名叫“甜来”,寓意自己的人生,已经苦尽甜来。
然而,让双生始料不及的是:苦尽和甜来,夭折了!连满月都没有出!
事情是这样子的:有天晚上,猛女子跟苦尽和甜来睡在一起。后半夜的时候,猛女子翻了一个身,就感觉后背被硌了两下,紧接着,又感到后背湿漉漉、黏糊糊的。猛女子赶紧惊坐起来,回头再看时,苦尽和甜来,已经内脏外露、血肉模糊,身体被完全压爆。
看到这幅景象,猛女子被吓得挠头抓脸,大喊大叫——猛女子,疯了。
双生在睡梦中被惊醒,看到眼前的景象,脑袋“咚”的一下,像被大锤砸中了一样,呆在原地。
旁边的猛女子,忽然从炕上跳了下来,大喊大叫着跑出门外。
装殓苦尽和甜来的时候,双生是用铲子把他们铲起来的——他们流出来的血,把身子和炕布牢牢地黏在了一起。
没过多久,双生自己也出了一场意外。
双生当时正在骟猪,被猪叫声惊吓到的猛女子,抱起一根大腿一样粗的圆木杠子,把双生的半个脑袋,从后脑勺那里,“咣咣咣”三下,砸进了腔子里。幸好有下巴顶着,要不然,双生的脑袋,整个都进去了。正是因为这场变故,往后余生,双生都只能一直仰面朝天。
双生的“娘家”人,看到躺在炕上、脸贴着腔子、奄奄一息的双生,全都哭了。
九妹哭着说:“哥,咱回家,咱不在贺家坡过了,猛女子疯了!”
其他人也哭着附和“我几个抬着你走!”、“现在就走!”、“走!”……
双生母亲只是哭,没有说话。
双生看看几个弟弟妹妹,惨然一笑,然后很吃力地叫了一声:“妈。”
双生母亲哭着探下身子:“我娃,啥事?你说。”
双生:“到底啥时候,才能真真正正苦尽甜来啊?”
又过了几天,双生正躺在炕上养伤,一高一矮两个公安走了进来。小个子公安进来就问:“你就是双生?”
双生心里一惊,赶紧坐了起来,回答道:“我就是,啥事?”
高个子公安弯下腰,对双生说道:“你的情况,我都知道了,按理说,这件事情,现在还不应该给你说,但是人家家属闹得太凶了——你媳妇猛女子,把人杀了!”
听说猛女子杀了人,双生瞬间觉得自己的头皮,像被人硬生生扯了下来:“啥?咋可能嘛?猛女子咋可能杀人嘛?!”
高个子公安:“猛女子在何沟,把一个二流子光棒的球给拔了,人直接就疼死了!还有两个二流子,蛋被踢得跟蒸馍一样。不过,这事不能怪猛女子,不用坐牢,就是得给家属赔偿一点丧葬费……”
双生:“那猛女子人呢?”
大个子公安:“在县精神病院。”
双生也不管自己的伤势,起身就往外走。两个公安赶紧拦住,大个子公安安慰道:“人没事,你放心!”
双生身子一拧,挣开了两人,淡淡说道:“家里的东西,都赔给家属吧,猛女子再瓜再傻,也是我媳妇,我不能让我媳妇呆在那种地方。”
大个子公安:“丧葬费没有多少,不用全赔,猛女子……”
话还没有说完,双生就已经跑远了。
到了精神病院,双生又是磕头,又是作揖,又是签保证书,花费了大半天功夫,才终于见到了猛女子。看到双生,猛女子“哇”的一声,扎进双生怀里,哭得跟个娃娃似的。
回到贺家坡,双生把贺把抓留下的大半家产,都赔给死了的二流子的家人做丧葬费,所有徒雇的活,也全部推掉了,安安心心在家照看猛女子。没活可干的黄牛,则租给其他徒雇,自己只收一些麦子、面粉、大米以及油盐酱醋做租金。
猛女子回到贺家坡不久,死了的二流子的家人和亲戚,跑到贺家坡闹过三次。头两次,双生把猛女子锁在了柴房,自己单独出来赔礼认罪。第一次,来了两个人,牵走了两头猪;第二次,来了七八个人,把所有的猪全牵走了;第三次,来了十几个人,全部都被猛女子吓得差点尿了裤子。
当时这十几个人,由一个身材肥胖、留着披肩长发、蓄着络腮短须、满脸横肉、双臂刺青的中年男人领着,砸开了牛棚,正要把牛牵走,结果被双生拦住了。
双生连连作揖恳求道:“好我的哥呀,给兄弟一条活路吧,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,把牛给兄弟留下吧!”
长发男一手牵着牛绳、一手指着双生,大声骂道:“留尼玛个黑批!你媳妇把我叔害死了,都没叫你苟日的偿命,拉你一头牛咋了?”
长发男又扭头看看周围其他人,大骂道:“你几个看尼玛的黑批呢?给我把苟日的往死里打!”
话音刚落,双生就被人一脚踹倒,其他人一拥而上,轮番对双生拳打脚踢。
就在这时,旁边柴房的门,突然被一脚踹开,猛女子像受惊的豹子一样,从里面扑了出来,对踢打双生的来人,又咬又挠。
不一会儿,再看猛女子,满嘴满脸都是血,也不知道是别人的血,还是她自己的血。有一个特别倒霉的,被猛女子“吭噌”一口,把肩膀上面一条揽筋给咬断了,胳膊当时就像一根面条似的,耷拉了下去,再也抬不起来了。
最后,猛女子抱起长发男,一个倒栽葱,将长发男的脑袋,“咚”的一声,重重地砸在了地上,直接就把长发男给砸晕了。
猛女子骑上长发男的后背,又把长发男的头发,连皮带血加肉,一把一把,全部给薅了下来。
可怜的长发男,刚被砸晕,又被硬生生的疼醒。实在遭受不住,长发男只能一口一个“姑奶奶”地求情讨饶。
其他人见状,早就一溜烟儿,全跑了。
打这之后,再也没有人敢找双生的麻烦。当然,大部分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,也都再也不敢过来串门。
没过多久,猛女子的肚子,又一天天大了起来。双生看了,也不说话,一脸的铁青。
大概过了七八个月,猛女子又生了,仍然是两个,仍然是一男一女,一对龙凤胎。不过,跟上次不同,这次生的两个小孩,又白、又胖、又壮实,最起码都有七八斤重。
生完小孩没多久,猛女子就死了,这是双生万万都没有料到的事情。
猛女子临死前,脑子忽然清醒了。看看身边两个不停啼哭的孩子,再看看门口背着脸看都不看孩子一眼的双生,猛女子难过地喊了一声:“双生。”
听到猛女子喊自己的名字,双生不禁心里窃喜:猛女子认得人了,疯病可能是要好了。但是,一想到猛女子生下来的两个孩子,身份不明不白的,双生心里又是窝气,头也没回地回了一声:“啥事?”
猛女子:“唉,算了,你把咱妈接上来,我有话给咱妈说。”
磨蹭了好半天功夫,双生才用驴子把母亲接到了贺家坡。
在前往贺家坡的路上,双生问母亲:“妈,到底啥时候才能苦尽甜来啊?”
双生母亲:“猛女子要是真的好了,我看就差不多了。”
到了贺家坡,看到两个刚出生的外孙,双生母亲高兴得直拍巴掌:“哎呀!猛女子,你啥时候生的?双生,你咋不早说?我还以为是啥事呢!”
猛女子看着双生母亲,一阵苦笑。双生则阴沉着脸,将身子背了过去。
猛女子让双生先出去,自己要跟双生母亲说几句贴心话。双生也不搭话,径直走了出去。
猛女子:“妈,我的疯病好了,彻底好了!”
双生母亲:“那好呀!那你一家子,就真的苦尽甜来了!”
猛女子忽然哭了:“妈,我怕是活不成了。”
双生母亲:“啊!咋了?好好的,咋就活不成了?”
猛女子:“妈,你好好给双生说说,俩娃都是他亲生的,让他不要胡思乱想,双生肯定听你的,求你了,妈!”
双生母亲听完,气就不打一处来,咬着牙说道:“原来是这么回事!苟日的双生!这事你放心,我保证能让苟日的灵醒过来!”
安慰了猛女子,双生母亲转头对着门口破口大骂:“苟日的,还不进来!自己撒的种,还不想认了?你到底算个人?还是六畜?”
听到母亲在骂,双生赶紧一路小跑,跑到了母亲跟前。
双生母亲指着两个孩子问道:“这俩娃,是不是你的?”
双生阴沉着脸,过了好半天,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:“是!”
双生母亲:“是就过来看一下俩娃!”
双生很不情愿地磨蹭到跟前,看了两个孩子一眼,很快又把头给背了过去。
双生母亲:“抱一下你俩娃!”
双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:“俩个娃,你叫我咋抱?到底抱哪个?”
猛女子忽然轻声说道:“双生,给俩娃娶个名字,行不?”
双生沉默了半天,扔下“野怂,杂种”四个字,转身冲出了门外。
猛女子猛地坐起身来,冲着门口大吼道:“双生,我摘尼玛!”
话音刚落,下身“噗”的一声,喷出一股又黑、又浓、又臭的血来,布满血丝的眼珠子,有一半都挤出了眼框,直接坐着就断了气。
双生母亲见状,赶紧一手堵着流血的地方,一手摇晃猛女子的身子。可哪里还堵得住?哪里还摇得醒?
等双生再回来时,猛女子的身子早已经僵了。双生母亲愤怒地拿起烧火棍,对着双生,边打边骂。
看到猛女子没了,双生连哭都没来得及,直接就晕死了过去。
再醒来时,双生也不说话,只顾着仰面朝天嚎啕大哭,从猛女子入殓,一直哭到下葬,不到一天,就把声音给哭没了。
随后,双生的眼睛里,先流出来的是眼泪,再流出来的是黄水,最后连鲜血都流出来了,直流得两只眼睛一团血红,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后来,贺家坡的泥腿子医生,用一把刮胡刀,把双生眼睛里面的血痂,全刮了出来,再用清水洗了好几遍。最后,左眼是保住了,右眼——彻底瞎了。
双生哭成了这个样子,猛女子的丧事,只能让双生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帮忙操办。
一切停当之后,双生母亲和弟弟妹妹们,都劝双生回“娘家”住,结果都被双生给拒绝了。
双生:“我这个人运气不好,怕把你们给连累了,再说了,猛女子埋在了贺家坡,我就得就在贺家坡陪着。”
双生母亲:“那俩娃咋办?”
双生:“妈,你放心,就算俩娃不是我亲生的,我也不会害俩娃,看在猛女子的份上。”
双生母亲:“猛女子临死叫我给你说,俩娃就是你的,看来说了也没啥用……”
一晃三年过去了,该给猛女子立碑了。双生推着独轮车,车子上面,一边坐着野怂,一边坐着杂种,三个人一起去镇上,给猛女子挑了一块青石墓碑。
在回来的路上,杂种就问:“爸,我妈有名字没有?”
双生:“有!”
杂种:“你有名字没有?”
双生:“有!”
杂种:“那你跟我妈都有名字,为啥我跟我哥没有?”
双生:“野怂跟杂种就是名字!”
杂种:“这倒算是啥名字嘛?现在村里娃都笑话我俩……”
猛女子的墓碑刚立好,九妹忽然披麻戴孝跑了过来,见到双生,直接就跪倒在地:“哥!咱妈没了!”
双生听了,整个人就像被雷炸了一样:“你说啥?”
九妹:“咱妈没了!”
双生眼前一黑,差点晕死过去。
在临死之前的几天里,双生母亲,总是做噩梦,梦到孪生、垫窝子、苦尽、甜来、贺把抓,还有自己丈夫。梦里这些人,都说想见双生,双生母亲就说:“见我可以,见双生不行!”
双生母亲把这个梦告诉了九妹,九妹就说:“妈,你这是一个人在家待太久了,没事你也出去转转。”
双生母亲没有听九妹的。
第二天,已经中午了,九妹做好了玉米粥、蒸好了馒头、切好了腌萝卜,去叫母亲吃饭,却怎么也叫不起来,一摸额头,手心传来一阵冰凉……
双生趴在母亲的坟上,边哭边埋冤:“你总说我能苦尽甜来,现在我还没有苦尽甜来,你就先走了,妈呀!”
哭完母亲,双生推着独轮车,车头上依旧坐着野怂和杂种,三个人也不说话,就往贺家坡走。
路过曹洼的时候,双生看到猛女子当年“糟蹋”自己的地方,已经被挖出了一个几十米高的陡坡。
双生忽然牙一咬、眼一闭,将独轮车的车头往陡坡一掀……
野怂和杂种,被倒下陡坡,骨碌碌就往下滚,一边滚,一边喊:“爸!”、“爸!”
双生丢了独轮车,也跳了下去,哭着喊道:“娃呀,咱三个一块去见你妈……”
斜坡的半腰上,根海背着大背篓,正在挖草药。看到一个大人、两个小孩,三个人正在飞快地往下滚,根海心里一惊,赶紧伸手紧紧抓住两个小孩。
抓住了两个小孩,大人也已经滚到了眼前。根海赶紧将两个小孩紧紧抱在怀里,背朝着大人,就势一坐。只听见“嘭”的一声,背篓直接被撞平,背篓顶部的箍藤,也“嗖”的一声,从根海的头顶飞了过去……
跳下陡坡之后,双生先是觉得自己的脑袋,在不停地转圈;然后,“轰”的一声,撞在了什么东西上面;紧接着,又是一高一低不停地颠;最后,终于落了地,彻底安静了下来。
双生慢悠悠地睁开仅存的左眼,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家的一张半新的草席上。双生想要翻身,稍微动了一下,浑身痛得像刀割了一样。稍微扭了一下脑袋,看到了躺在旁边的野怂和杂种。
双生赶紧爬过去,用力摇晃着两个孩子:“野怂!杂种!野怂!杂种!”
摇晃了半天,野怂先醒了,杂种紧接着也醒了。
杂种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爸,我妈在哪呢?”
一句话,听得双生心如刀绞。双生正要说话,根海带着梦龙,两个人缓缓走了过来。
双生赶紧爬起来给根海打招呼:“叔……”
根海摆摆手:“躺着躺着,你跟娃咋从坡上滚下来的?”
双生:“你侄活得太苦了,不想活了。”
根海:“俩娃叫啥名字?”
双生:“大的叫野怂,小的叫杂种。”
根海气得一跺脚:“你咋给娃起这样的名字?”
双生委屈巴巴地回答:“就不是我的,你叫我咋起名字?”
根海:“行了行了,先问问猛女子是咋回事。”
只见根海点了一根红蜡烛,滴了两滴蜡油,将红蜡烛栽在了双生旁边,然后盘膝坐下,又从怀里掏出一张黄裱纸,放到红蜡烛上面点燃了,“轰”一声,塞进了嘴里。
根海慢慢闭上眼睛,忽然又猛地一睁,用猛女子的口吻怒骂双生:“摘尼玛!还认得我不?”
双生战战兢兢地回答:“你是猛女子?”
根海:“不是我,还能是谁?!”
双生:“你在那边好着么?”
根海:“好个锤子!我死不瞑目,你看你给娃起的名字,野怂、杂种,咋?娃不是你的?”
双生:“村里好多人都说不是。”
根海:“咋?不是你的,还能是那几个耍流氓的二流子光棒的?”
双生:“都这么说。”
根海:“说尼玛个黑批!那几个二流子光棒,球都被我给拔了,你又不是不知道,还听村里人乱嚼舌头!”
双生:“你说的有道理,那俩娃为啥长得跟我不像?”
根海:“你长得像你爸不?”
双生:“不像,我像我妈。”
根海:“那你还要求娃长得像你?”
双生:“你这么一说,我就明白了,是我冤枉了俩娃。”
根海:“那你说,接下来你应该干啥?”
双生:“我应该干啥?”
根海:“给俩娃改名字么,瓜皮!”
双生:“对对对,现在就改,现在就改,你……”
双生还想说话,只见根海把眼猛地一闭,过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睁了开来,嘴里“噗”的一声,喷出一股青灰。
根海:“猛女子走了,临走说的话,你都记住了?”
双生拱拱身子:“记住了!”
杂种爬上双生的肩头,好奇地问道:“爸,你刚才跟谁说话呢?”
双生笑着摸了摸杂种的脑袋:“跟你妈。”
根海忽然问道:“双生,你得是还有一对儿女?”
双生:“有,大的叫苦尽,小的叫甜来,还没出月,就折了,猛女子也是因为这事疯的。”
根海:“哦,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
根海一把抱过杂种:“走,给你看个异门儿。”低头再看看野怂:“你也一块来!”
根海带着两个小孩出去了一会儿,一个人又回来了。
双生神色紧张地问道:“叔,俩娃呢?”
根海笑了笑:“耍累了,睡了。”
根海朝坐在旁边的梦龙招招手:“梦龙,来,帮叔一把!”
梦龙走到根海跟前,盘膝坐下。根海照例从怀里取出两张黄裱纸,一张点燃了塞进梦龙的嘴里,一张点燃了塞进自己嘴里,两人同时闭眼,又同时睁眼。
只见根海怒目圆睁,对着双生大声问道:“双生,还认得我不?”
双生摇摇头:“不认得。”
根海:“我就是被你踢下炕,摔死的孪生!”
听到“孪生”这个名字,双生心里就是一紧。
根海指指旁边的梦龙:“知道这是谁不?”
双生摇摇头:“不知道。”
根海:“这是咱妹子,喝榆树面糊糊撑死的垫窝子!”
双生听完,顿时双手颤抖、热泪盈眶:“哥呀,妹子呀,没想到咱们,就这么见面了!”
梦龙一动不动,没有搭话。
根海:“你没想到的事,还多着呢!记得苦尽跟甜来么?就是我俩托生的,托生的时间不对,所以连月都没出。然后又托生了一回,被你起了野怂、杂种这两个烂名字!”
双生:“哥,兄弟的罪太大了,你说我现在应该咋办?”
根海:“咋办?好好过你的日子,把俩娃养好就行!不说了,我俩走了。”
双生:“哥,咱妈……”
双生还想问问母亲的事情,只见根海和梦龙,同时闭眼、睁眼,然后嘴里喷出一股青灰。
根海:“双生,你哥跟你妹子说的话,你都记住了?”
双生:“记住了,记住了,以后我一定好好过日子!”
根海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枚白色的丸子,对双生说道:“这里面有条苦虫,你咽下去,等苦虫长大了,咬掉你肚子里的苦果、苦枝、苦叶、苦根,慢慢你就不觉得自己活得苦了。”
双生用双手捧过白色的丸子,往嘴里一放,一扬身,“咕滋”一声,咽了下去。
白色的丸子一下肚,双生就觉得浑身的毛孔,像被涂满了清凉油一样,无比的舒畅。
野怂和杂种忽然跑了过来。
杂种:“爸,咱啥时候回?”
双生:“现在就回,现在就回!”
双生转身问根海:“叔,咱家的水担和粪笼借我一下行不?”
根海:“行!就在后院,自己拿去。”
双生领着野怂和杂种,去了根海家后院。再回来时,双生肩上挑着一条水担,水担前面的粪笼里坐着杂种,后面粪笼里坐着野怂,一路不停地发出“吱扭”的响声。
走到根海面前,双生停了一下:“叔,我走了,水担跟粪笼后个还你。”
根海:“不急不急,你身上的伤,现在能走不?”
双生:“没事,都是皮外伤。”
根海:“行,那你跟娃慢点,记住,好好过你的日子。”
双生:“行,记住了,我走了……”
在水担的“吱扭”声中,双生问野怂和杂种:“给你俩改个名字,行不行?”
野怂:“行太太。”
杂种:“野怂、杂种,难听死了。”
双生:“牛牛娃叫苦尽,女子娃叫甜来,你俩看咋样?”
“甜来?好!好!好!”杂种拍着巴掌,一个劲儿地叫好。
野怂努了半天嘴:“苦尽?也行,反正比野怂好听多了。”
双生:“苦尽、甜来,跟爸说,你俩想吃啥?”
苦尽:“碗子肉么,我还没吃过。”
甜来:“九姑说,碗子肉底下要放红薯,上面要浇蜂糖。”
双生:“行,这就回去给苦尽跟甜来,做碗子肉!”
双生以水担的“吱扭”声为节拍,忽然唱起了不知道谁编的童谣:“碗子肉,就是香。猪肉荤,放生姜;红薯甜,浇蜂糖。一嘴油,一嘴糖,吃饱上山能打狼;先牙疼,再滑肠,疼毕拉完心还想,一顿不吃闹得慌……”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eqimingxing.net/tpszdzz/9732.html